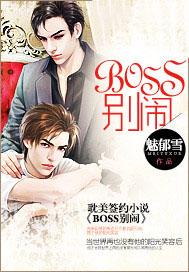腐书网>穷鬼一个 > 被捡回来(第3页)
被捡回来(第3页)
没娘的小孩不算小孩了,所以她自己一个人迎着夕阳摸去了,在那里没刨出尸体,都是血,还有苍蝇丶老鼠,臭气熏天。
文玉雁是怕老鼠的,在家里文娘会拿着鞋,在它们爬上床之前拍死。小安安也提议过,找到老鼠洞一网打尽,一只老鼠都跑不了了。文娘就笑,说,老鼠杀不完的,它们能杀完,我们在这里也早就死了。
她那时忽然就不怕老鼠了,因为觉得它们是自己的同类,大家都在艰难地活着。同类怎麽会怕同类呢?除非它们是和那些放狗咬死自己爹的人一样的同类。
小孩指甲软,很快就裂了,甲身劈成两半,指缝里渗进去血。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尸体上的。文玉雁想,老天奶,求求你了,让我找到我娘吧,我就看最後一眼。
老天奶没开眼,开眼了也不会看一只孤儿小老鼠。文玉雁最後也没找到,只能找了一个跟娘体型差不多的人,脱了褂子盖住她的脸,抱着她的胳膊放在自己身上,像是娘在拍自己。
其实尸体的脸已经看不清了,是不是真的文娘也不清楚。文玉雁盖住脸只是因为她会联想到娘的脸也是这样的,小小的心会痛。
很饿,很渴,努力祈祷着跟娘一起死也能在地府相会,离开人世寻找自己最後的丶唯一的归属,奄奄一息之际被沈至景捡了回去。
他说了很多事,说自己希望做个剑客,找到墙外的自由,做一只翺翔的鸟,飞往任何地方。
文玉雁于是点点头,说他很有剑客的气质,肯定能完成自己的梦想。
沈至景就瞬间红了眼眶,狠狠地摸了一把泪,看向角落里的一堆废纸。那是他珍藏的话本子,被威严的母亲翻出来就变成了一堆碎屑。
偌大的沈府,上至家主下至侍人,没有一个人不惊诧于他的怪异,认为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都是小公子何不食肉糜的産物,躺在长辈的温床下幻想不切实际的愿望。
他被路过的姐姐嘲讽,说比起这些东西,最重要的就是多留心自己的容貌,将来好做个联姻工具。
稚童没有继承权,姐兄又已长成,共同接过了府内的重担,他所依靠的唯有母亲的疼爱,在府内几乎没什麽话语权。
他听到过下人的窃窃私语,议论自己是个失了心智的小疯子,握了握拳头後也只是默默地离开了。
有人居然肯定了他的梦想,像昏暗的屋子里投进来的一缕阳光。
他吸了吸鼻子,仰起脸露出一个明媚的笑,道:“你现下可是好多了。我去那里的时候,看到一个起伏的尸体,差点被吓坏。挪开她後,看见下面有个人在呼吸。想了想还是你背了回来。
“我们差不多大,不过你可真轻,好像一点肉都没长。”
文玉雁心道,也许老天奶的那边的时间流速和凡间不一样,後来派了沈至景来救她,成功进入了文娘生前在的沈府。
她希望能找到母亲的名字,这样就连死亡都不怕了,再黑的路,都有最爱的人在前面守候着。
摔下去疼不疼,她希望经历一次娘的疼痛,下去之後对她说,我不是小孩了,我是跟你死法一样的鬼。
沈至景的话倒是让她倒是想起了隔壁小孩,她也这样对自己讲过,一个没自己大的小女孩。没有名字,就叫红薯,因为她娘生她前在吃红薯。
顶饱又便宜的红薯,村里人都吃。红薯娘爹在她三岁的时候死了,没有人知道怎麽死的,稀里糊涂死掉的人多了去了,大家也见怪不怪了。红薯成了孤儿,她是文玉雁唯一的朋友,文娘上工後,只剩两个孤单的灵魂相互依靠。
这个可怜的孩子其实话很少,在田埂上坐一个下午才支支吾吾突出几句不连贯的话,但每个字都倾注着最真实的情感,比得上宴席间觥筹交错丶阿谀奉承的一万句,她说什麽文玉雁都会耐心地听完。
红薯变成孤儿的那天,没有哭,就是怔怔地握着小木棍,在沙地上画圈。直到文玉雁过去找,她才放下了木棍扑到怀里。文玉雁只能摸着她干枯的头发,大一点的孩子也不代表就比小孩子懂得更多,根本不知道该做什麽。
直到文娘回来,文玉雁拉着红薯,两人一起跪在风尘仆仆的女人面前。文玉雁请求文娘能接济一下红薯,她很瘦,吃得很少,一点点就够,大了还能给家里干活。
文娘很快就同意了,温声道你们快起来,地上很凉的。她没说多馀的话,很自然地接纳了这个孩子。红薯夜里就跟文玉雁抱着,两人相互取暖,紧紧地抱着躺在床上,文娘就着一点蜡烛的微光缝衣服,屋子里比眼下要冷得多,文玉雁却觉得挺好的,一家三口都在。
红薯抱着文玉雁的腰,她感觉凉凉的,才发现沉默了一天的红薯居然哭了,泪水沁透单薄的衣衫,小小的孩子又手忙脚乱地去擦。
她不在意衣服,她想抱抱红薯,说你不要哭了,瞎子说睡觉前哭不好的。舌尖上的话却被文娘制止,她放下了针线活,俯在两个孩子身上拍了拍红薯的背,说:
“哭吧,孩子,哭出来就好了。”
文娘看上去很有经验,拍人也很温柔,红薯哭着哭着睡着了。文玉雁没睡着,她就躺在娘的臂弯里,她的怀抱很温暖。
文玉雁问,她小名叫红薯,我小名叫安安,那麽你生我前吃了什麽?文娘笑了笑,说,是平安的安呀,我希望你一世平安。母女都是文盲,那天後却共同记住了这个字。
红薯比安安小两岁,三岁失亲,五岁时被她的远房亲戚接走了,也就是一年前。
小女孩寡言,但在那天上船前,对她唯一的朋友说了很多,离开前两人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手,直到被强硬地分开。
也就是那天,文玉雁突然发现,原来自己和娘都没亲戚,第一次接受到一些人方面的知识。
可惜红薯走後,她再次变回了孤单的小孩,唯一的知识也毫无用武之地。村里这麽大的孩子都去上学堂了,当然,跟沈至景这种高门公子不是一种。
文娘没有钱,她们能活着就是竭尽全力,女儿自然不会怪她,只会心疼那日渐佝偻的腰。没人的时候就去找村口瞎子聊天,可惜瞎子不久後也死了,她死前还把当年给文玉雁算命的钱还了回去,说安安是个好孩子。
三个铜板,文玉雁给了文娘两枚,留下了一枚做自己的朋友,就对着它说话,没人回应,更加寂寞了,最後一个铜板也被交给了文娘,填饱不了心里的寂寞,至少能换一点东西填饱肚子里的寂寞。
所以她现在揉了揉多愁善感的沈至景的头,因为文玉雁体验过这种日子,倾诉却没有回应的事很难受,不希望新朋友和自己一样孤独。
瘦小的人和记忆中文娘的身影相重合,文玉雁闭了闭眼睛,轻声道:“哭吧,哭出来就好了。”
哭出来就好了,泪水会无孔不入填满所有的沟壑,抚平内心的伤痛,滋润干涸的土壤,哭吧,哭出来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