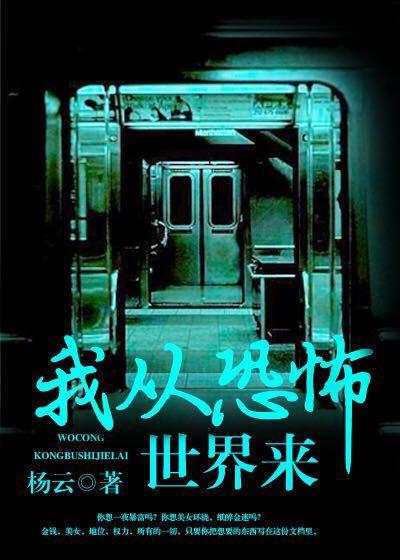腐书网>梦长安官网 > 第 28 章(第3页)
第 28 章(第3页)
阿肥倒是自在,一路打量着皇宫的风物景致,口中不住啧啧有声,似乎是颇为不屑。
走过一座东西穿堂,仪门内有大院落,上面五间大正房,两边厢房鹿顶,耳门钻山,四通八达,轩昂壮丽。
内监将迟瑞引入堂屋:“哥儿先在这候着,等咱家通报一声。”
迟瑞无声点头,擡眼四顾。只见这屋内陈设异常奢华,临窗一张贵妃榻上铺着猩红毛毯,正面设着大红引枕,秋香色绣了合欢花的褥子。两边设一对梨木小案几,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,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,里面插着时鲜花草。
地面上整齐摆了四张大椅,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,底下四副脚踏,两边又有一对高几,几上茗碗瓶花俱备。
看见迟瑞进门,马上有宫娥过来奉茶,又有宫人拿了软枕,与他靠背。
迟瑞不敢落座。
阿肥却大大咧咧蹲到那张贵妃榻上,左看右看,评价道:“别的都一般,就此处还不错,比暖春阁强些。”
约莫坐了一盏茶时间,适才出去那内监回来了,忙忙朝迟瑞招手:“皇上那边传饭了,哥儿快随我来。”
阿肥听说有饭,马上咻的一声,飞到迟瑞肩头,老实蹲着。
内监携迟瑞出後房门,由後廊往西。
但见前头崇阁巍峨,层楼高起,琳宫合抱,复道萦纡。正面一座玉石牌坊,上面龙蟠螭护,玲珑凿就,写着“承香殿”三字。
内监引着迟瑞拾级而上。
迟瑞一路低着头,快到楼梯尽头时,才发现上面一身黑衣蟒袍的守卫竟是晁风。
迟瑞小心翼翼的擡头看了他一眼,紧张的揪住自己披风上的毛边,咽了口气。
晁风身姿笔挺,目不斜视站在楼梯尽头的白玉护栏一侧,待得迟瑞从身侧过时才小声说了句:“不必紧张,萧允鹤就在里面,他会保你周全。”
迟瑞诧异的回头。
晁风已放远了目光,不再说话。
内监将迟瑞引入殿内,高声宣道:“皇上,萧国师家眷带到——”
殿内有人沉沉一声:“知道,退下罢。”
内监躬身应是,退了下去。
迟瑞低着头,正不知所措,又听那人问道:“你便是萧国师的弟弟,模样倒是俊秀。过来罢,你兄长可是候着你候得久了。”
迟瑞心头茫然:兄长?……
擡眼,只见殿内已经摆下数张沉香木案,上面设着杯箸酒具等物。每张案桌前均有两三个宫娥煽风炉煮茶烫酒。
正殿中央一张案几,端坐着个身着龙袍之人,料想便是当今天子,适才与他说话之人。
天子一侧,是杨妃的坐席。
允鹤端坐在李隆基下手的第一张宴席上。
再下来,一右一左便是杨国忠与安禄山。
迟瑞眼神馀光瞟到杨国忠的身影,脸色顿时白了。他留意到,允鹤身侧尚有一空位无人入席,却不敢就此走过去,悬着一颗心站在原地。
允鹤见他来了,起身去迎:“今日天寒,怎的不多穿件衣服?”
迟瑞今日一整日均在云雾当中,此刻看到允鹤,心里方才安定些了。
还未说话,便听李隆基大笑开口:“萧国师,适才一路上,朕问了你多次,可要什麽封赏,你都推说要等你这位幼弟到来,如今他已来了,想要什麽,你大可开口向朕要。”
李庭瑄适才听允鹤言谈中提到自己的弟弟,此刻看到迟瑞进来,不由多看几眼,只见这少年双眸纯透,如小鹿一般的存在。
暗忖:这般气质,倒像是一家人。
允鹤携了迟瑞的手往前几步:“你随我来。”朝着殿前天子微一拱手,“其实这少年与我并无血亲,他乃前尚书郎迟明玉之子迟瑞。”
他这话一出,在场所有人俱是一震。
杨国忠脸上顿时变色。
他决没想到,这个由他亲自开了条子插队进来的少年会真的当上国师。而他当上国师之後的头一件事,竟然是来翻他的旧账。
李隆基微皱了眉。这些来甄选国师的人,怎的个个都另有目的,头一个弹劾安禄山,此番又来弹劾杨国忠。
允鹤面色从容,对衆人反应显然并不意外。
迟瑞被他握在掌心的手抖了下,似迫切想从中抽离。
允鹤反掌将他动作压下,继续说道:“昔日迟尚书被杨相国以书画谋逆之罪判刑,家眷或是变卖,或是流放。这少年与我颇有机缘,被我救下後便一直跟在我身边。虽可衣食无忧,却终究是戴罪之人,入了贱籍。皇上问我要什麽封赏,是否有所求,那我所求便只有一事。当年迟尚书书画之中是否有谋反之意,功过是非已难追溯,纵有过错,罪不及其後裔,便请皇上恕了小瑞无罪,让他脱离贱籍。”
他话刚说完,迟瑞脸色惨白,用力挣出自己的手,急切的摇了摇头。
他记得很清楚,当日被抄家时,家中老管家曾替父亲申辩过几句,结果当场就被羽林卫用刀柄敲碎了一口牙,打了个半死。
允鹤并不看他。他的站位比迟瑞略前了半个肩头,一脸的泰若自然。
杨国忠脸色一变再变,终是忍不住开口:“你……简直荒谬!谋逆之罪,乃诛九族的大罪,吾皇仁慈,仍让他留下後裔,已经是开天恩了!”
杨玉环忧心忡忡,偷看了眼李隆基的脸色:没想到这新晋的国师,竟是冲着自家哥哥来的。与虢国夫人交换了个眼神,两人均是一脸愁容。
安禄山看到允鹤矛头竟是直指杨国忠的,倒也乐见其成,插话进来:“我是胡儿,不怎麽识字,却也时常觉得那因为一幅画,几个字的意思就把人当做反贼的事情,甚是荒唐。是以似我这般不会说话,心直口快之人,在这朝中,是时常惶惶不可终日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