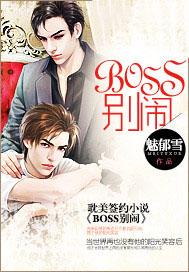腐书网>暴雪天讲的什么 > 第4章(第3页)
第4章(第3页)
“城市里有城市里的规则,大家都忙,除了至亲没人关心你的死活;出来玩不一样,一个车队就是一个家,做不成家人的人我们压根就不会带出来。这里也有这里的规则。”
曾不野认真听着,意识到自己给他添了麻烦,让他担忧,于是真诚道歉:“对不起,我真的不知道…”
“没事。你早晚会知道。”
徐远行绕到另一边,拉开她副驾的门坐上了车。他只喝了酒,几乎没吃东西,肚子咕咕地叫,叫声在静谧雪夜里格外醒目。但他还是说:“你要是想练冰面漂移,先学会把车走圆。你每次转弯有棱有角,不像在飘。”
“我不练了。”曾不野说:“我到时闭眼。”
她很有一些冷幽默在身上,人也实在是一把犟骨头。徐远行批评她的时候她老实听着,他消气了,她又开始气人。
徐远行被她这句噎得直点头:“行行行,你牛逼,你了不起。你到时好好闭眼。”
曾不野就笑了。
这一次没像上一次一样莫名地笑一下,这次笑声持续久了些。虽然很怪异,但徐远行还是鼓励了她:“多笑笑。笑起来多好看。”
“你看见了?”曾不野问。
“…没有。”
曾不野撇撇嘴说:“我不太会笑。”
“你面瘫啊?”
“你不会说话可以闭嘴。”
这下轮到徐远行哈哈大笑了。
在城市里这样的笑声太罕见,在这里又觉得不突兀。他的笑声是属于天地的笑声,能让见者心情朗阔。
“我损你你别生气,我没恶意。”徐远行说。
“我损你你也别生气,我有恶意,我就这样的人。”曾不野说。
徐远行不跟她一般见识,因为他的肚子又叫了,咕噜噜的声音,很是不收敛。曾不野不忍心他再挨饿,就问:“你给我打包什麽了?”
“那可是有肉有菜有土豆…还有汤。”
“有面条吗?”
“你能不这麽事儿吗?”徐远行切一声。
曾不野决定不逗他了,她知道那打包的饭菜已经凉透了,可以拿到餐厅热一热,跟大家一起吃。
他们到的时候,赵君澜已经吐了两轮了,群里把他的醉状做成表情包开始刷屏,线上线下联动。绞盘大嫂已经带着小扁豆去睡觉了,剩下的男男女女热闹说笑。
前面立着一个箱子,徐远行说那是孙哥昂贵的吉他,他仗吉他走天涯,再过会儿酒都至酣处,就该轮到孙哥带着大家唱歌了。
有人看到曾不野进来,就招呼她:“野菜姐,你是铁打的身体吗?你不饿吗?”
曾不野对他点点头,坐到了角落里。徐远行招呼服务员去热菜,其馀人打趣他:徐队功力不行了啊,请个人要这麽久。
徐远行自然不会说中间的插曲,不然显得他和曾不野都是大傻子。他倒是很高兴有个插曲,理所当然躲过两轮酒。他坐在曾不野身边,用胳膊肘碰她一下:“曾姐你来说一下,为什麽你这麽难请?”
一会儿野姐丶一会儿菜姐丶一会儿野菜姐丶一会儿曾姐,自由切换,问题是这些人竟都能同频,也起哄:对,曾姐你来说一下。
曾不野就直说:“我去练车了。”
“为什麽?”
“因为我要问鼎武林。”
大家都很安静,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起初都觉得这姑娘看着有点病丶不爱说话丶很执拗,是个不好相处的主,也实在不像这款车的车主。她太内敛丶太安静了。
这一句“问鼎武林”倒是显出了她性格里的三分豪气,或许这个人并非她表现出来的那样不好相处。
徐远行见她自己招了,就也顺杆爬:把她在空场地压弯的情形添油加醋说了,还说:你们见过後海边遛弯的老大爷吧?咱曾姐压弯就那样。
“比老大爷快点儿。”曾不野纠正。
“快点儿,有限。”徐远行说。他手机一直响,振得桌子嗡嗡的,偏巧曾不野听不得这种声音,这会让她紧张。见徐远行没有接的意思,就说:“你能接一下电话吗?如果你没聋的话。”
徐远行翻起来看一眼,按了。
电话又响,他再按。
人这样,多半是在驯化对方。原谅曾不野用“驯化”这个词,因为她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几乎都是一场相互驯化的过程。谁依附丶谁掌控,自有它的流程。
“接电话。”曾不野说:“不然就把手机丢一边去。”
趴在桌上躲酒的赵君澜闻言忍不住擡起了头看曾不野。大家出来玩,大多其乐融融,没人会管别人接不接电话的闲事,更何况是用这样的口气,对青川车队的队长徐远行同志一点该有的尊重都没有,也没有新人初来乍到小团体的诚惶诚恐。
这女的到底干嘛的啊?赵君澜第一次对车友的身份産生了好奇。
徐远行倒不意外,他已经知道了曾不野是什麽德行,但他偏不接,还小声说:“你少管闲事。”扭脸看着曾不野,看到她耳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,想了想,就起身把手机放进了一边的餐柜上。
“谢谢。”曾不野说。
“不客气。”
赵君澜这才明白:曾不野根本不在乎也不好奇那电话为什麽响,只是那震动声令她不舒服。她真的在生病啊。跟徐远行交换了一个眼神,意思是让徐远行跟他出去。
徐远行起身跟了出去,两个人站在走廊无人的尽头。赵君澜手指了指包间方向,压低声音问:“野姐不会有什麽事吧?我的意思是不会给咱们惹什麽麻烦吧?”
“你怕她想不开死了啊?还是怎麽着?”徐远行问。
“我说不清,我觉得她有病。之前是开玩笑啊,今天我真觉得她有一些反应跟别人不一样。”